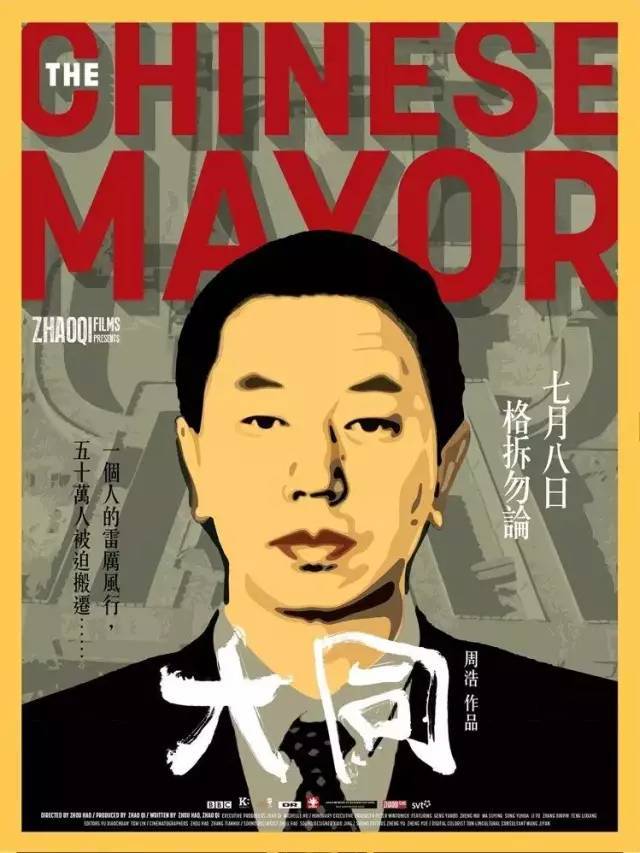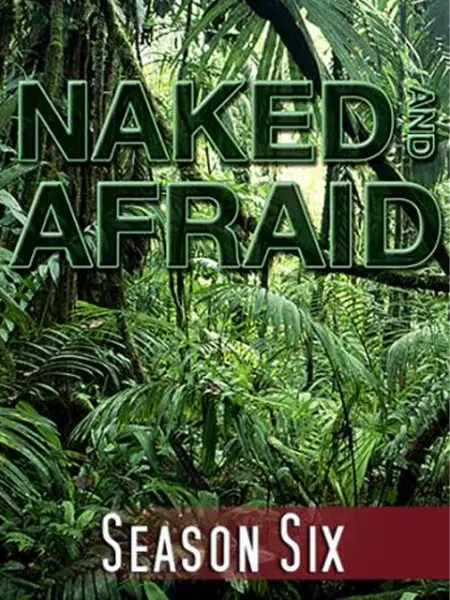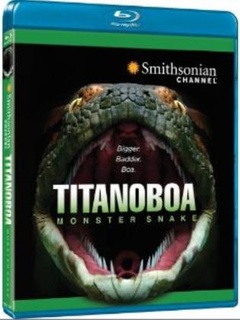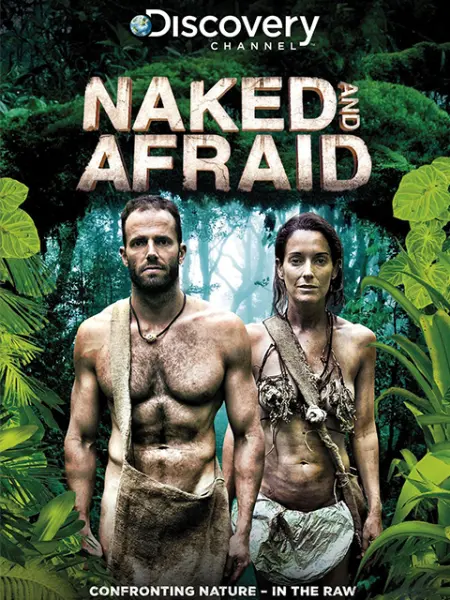@《第四公民》相关热播
@最近更新纪录片
@《第四公民》相关影评
最近,艺术家James Bridle模仿美国国家安全局(the National Security Agency, NSA)的大规模公民监视模式,为伦敦南岸中心(Southbank Centre)创作了一个网上艺术项目——Citizen EX(citizen-ex.com)。在这个网站上,你可以下载一个软件嵌在电脑的浏览器上,它会根据你浏览的网页,进行计算和归纳,显示你在网络上的“国籍”或公民身份。 显然,这不同于传统意义上根据出生地、父母的国籍或血缘等因素来认定的公民身份;这个软件显示出来的结果,是一种新形式、“基于算法的公民身份”(algorithmic citizenship)。它根据你浏览网页域名的实际位置,进行实时的数据搜集、计算和归纳,来告诉你,你在网络上是哪国人。 世界上大多数人只有一个国籍。但这个网络计算得来的公民身份并不像传统的国籍那样单一和固定,在不同的时候查看结果,你的公民身份是不同的——它一直在变化、改写,是一个掺杂了不同比例(且比例不停变动)的数个国籍的组合,可能随时有新的国籍以某个比例加入进来,也可能某个国籍过几天又消失了。你会发现,你的公民身份是一个莫名其妙的各色国家大拼盘。“.scot” 网络虽然看似是虚拟的,但网络世界也是兵家必争之地。Bridle给我们讲了苏格兰独立运动中的一个故事,来告诉我们网络上的国界是怎么划分的: 早在我们现在熟知的万维网出现之前,我们用一连串数字形式的IP地址来标记网站和计算机。随着计算机和网络的增长,DNS(Dormain Name System,域名系统)于1983年出现,使用至今。DNS把网址名称转换为IP地址,那些代表网址的数字仍然在那里,只是被藏到了网址名称后面。这些名称也是有含义的,比如“.com”, “.net”和“.org”,代表不同形式的组织。人们认为DNS应该也要标识计算机的位置,于是1985年,第一个国家顶级域名(country code top-level domains, ccTLDs)被注册了,就是代表美国的”.us”,还有代表英国的“.uk”,代表以色列的“.il”。第二年,.au,.jp,.de,.fr,.kr等等,都出现了。到今天,一共有270个国家顶级域名,分别代表着每一个被承认的国家。 “被承认”十分关键。当年,南加州大学的计算机科学家们,为了确定哪些地方可以算作一个主权国家来给其分派域名,使用了国际标准组织颁布的、由联合国认可支持的国家名单“ISO 3166-1”。然而这样处理的问题是,那些不被承认、新出现的,或未来可能独立的国家怎么办呢? 从2009年开始,苏格兰的一群商业机构开始游说“互联网名称与数字地址分配机构(the Internet Corporation for Assigned Names and Numbers,ICANN)”,要给我们分派一个“.scot”国家顶级域名才行啊。这个活动受到了苏格兰政府、文化和商业机构以及很多苏格兰民众个人的大力支持,他们认为这意义重大,是世界各地的苏格兰民众、机构和商业组织明确地在网络上定义自己身份的机会。 到2014年,ICANN在英国政府正式表示“不反对”的情况下,将“.scot”域名授予苏格兰。几个月之后,苏格兰政府迅速把它们自己的网站域名转移到了“gov.scot”,与英国政府的“gov.uk”区分开来。 不过历史弄人,当年9月,在决定苏格兰是否能成为一个独立国家的历史性公投后,它被留在了联合王国。有意思的是,独立和统一的双方阵营在竞争激烈拉票过程中,都在网络上使用.scot这个域名;而苏格兰独立的努力失败后,政治组织或事件是选择使用“.scot”还是“.uk”域名就不仅仅是一个文化上的选择了。网络上的内容受到其注册地所在国家的法律限制,尤其目前爱丁堡和伦敦在英国的人权法案(涉及与公民隐私相关的法律规定)上尚存多种分歧。而2015年中期选举后,保守党单独执政,苏格兰独立党在国会占有56个席位,这个局面有可能最终导致两地制定不同的网络隐私的法律。用户在注册于不同国家的网站上能发布和分享的内容是不一样的,在网络上的隐私和人权能受到何种保护也是不一样的。 从苏格兰国家网络域名的故事里,我们可以一窥公民权利、政治和互联网深刻复杂的交织博弈的关系。也正在这个网络空间分派域名、“划分”了国界的前提下,才得以将用户划拨到各个以国家为基础的类别/群体里,给他们一个国籍/身份,决定用户应该遵守哪国法律;不管是国家还是商业组织,才能确定哪一套法律、治理体系应该施加在用户身上。 如Georgetown法学院教授Julie Cohen在《隐私何为(What privacy is for)》这篇文章中指出,网络公民监视不仅是侵犯隐私,并且是一种知识生产模式,以及生产出某一种特定的主体的治理模式。其目的是生产出可追踪、预测的公民-消费者,其偏好的自决模式遵循着可预测的、可生成利益的轨道。 Cohen进一步分析了公民监视和信息资本主义(information capitalism)的结合,达到“去民主化”和“去政治化”的效果,对自由主义民主造成伤害。这种结合在民主社会创造了一种“调节的民主”,形成“技艺高超的社会知识变阻器,能够将信息环境调整至每个人的感到舒适的程度”;而自由主义民主公民权要求存在一定程度的“不适感”,这种不适感要强大到足以激发公民去为了政治和社会理想而推动进步。调节的民主社会中公民则因为环境中信息消费的“舒适感”而缺乏去实践这种公民权利的渴望,他们也不再是自由主义民主政治传统培养出的那种公民,他们在商业和政治利益体无处不在的监视和管制下形成的偏好,与真正的公民的独立决策大相径庭——公民独立判断和决策是通过富有活力的公开辩论形成的,这也是自由主义民主得以存续和完善的必要条件。 政治和媒体学者Jodi Dean从另一层面分析了信息资本主义,或称传播资本主义(communicative capitalism)深刻的去政治化作用。她认为网络通过为用户制造信息丰富、政治参与和全球整体性等幻象,导致传递出的信息和观点无人接收、没有回应,信息消费包裹了所有政治努力,致使民主政治的实现异常困难。 我们再回看苏格兰独立公投。Bridle没有讲的故事是,在2014年历史性的苏格兰独立公投前,支持独立和支持统一的双方阵营争取投票期间,独立阵营在社交媒体上一直占有明显优势:截至2014年9月8日的前5周里,在Facebook上,独立阵营在苏格兰生产了205万条互动信息,而统一阵营有196万条。在Twitter上,这种差距更为明显——据社交媒体分析公司Crimson Hexagon统计,在公投日(2014年9月18日)的前一个月里,独立阵营占据了90%的关于公投的信息。 但最终,统一阵营以55.3\%的得票率赢得了胜利。独立阵营在网络上创造的互动、赢取的支持并没有很好地转化为实际的投票行为。当然统一阵营的成功有多种复杂的原因,但独立阵营在网络空间的遥遥领先,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了其对局势的预估和关键阶段的竞争策略。 这看上去很讽刺——当年苏格兰刚刚在网络空间争取到了“主权”(苏格兰国家顶级域名),转眼现实中建立主权国家的政治努力,被两位学者揭示的信息资本主义的去民主化/去政治化作用如消费主义式的滤网一般弱化了。元数据 美国参议员Ron Wydon在接受卫报采访、评论斯诺登揭发的NSA大规模公民监视时提到“元数据(meta data)”这个概念。其原本的定义是关于数据的数据。具体在这个NSA监视的案例里,指的是被监视者(在监视系统里通过数据形式显示)的不停变动的社会关系(也显示为数据)。 “当政府知道不光知道你的身份,还能实时获知你在什么时候联系谁,都谈了些什么,你的社交网络,并由此搭建起一个关系网,那他知道的真的太多了。” 密歇根大学的John Cheney-Lippold教授引入福柯的软性身体政治(soft biopolitics)的概念,来揭示获取公民在网络上的社会关系信息,也就是公民的“元数据”来施加的更为“精巧”的治理术。 大家都知道,现代社会的权力机构是通过间接的、无形的治理术来对人进行控制和规训。NSA根据元数据对用户进行控制分类(cybernetic categorisation),也就是根据网络用户不断变动的对某个国家或组织的从属关系,以及他们变化中的社会关系,随时对其进行计算、分类、定义,再计算、再分类和再定义,在其社会关系的随机性里生成新类别和新定义,在此基础上随时不断调整对待用户的方式。 Cheney-Lippold认为,控制分类本身就是一种身体政治的尝试,因为控制分类对用户并不是通过一次性的感应数据来分类的,而是与类别进行连续不断的互动和修正,类别的含义可以根据针对某些内容和人群的编码和算法模式重新调整,持续为现有政策如何作用于主体提供新的方式。建立在分类基础上的政策因而可以自动地和持续地重新定位,来处置和作用于新的人群。 我们可以看到,在Citizen EX这一项目里,用户显示出的网络国籍/公民身份并不稳定单一,而且模糊和持续变动。但不管你的国籍/公民身份如何变化,成为哪种组合,都可以被数据分类囊括起来,进而被定义,然后被施以某种相应的治理术。NSA监视公民社会活动和社会联系所获取的个人数据和信息也是动态多样的。按照NSA的说法,公民监视是为了及时找出“有可能”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的人。而他们如何在人海茫茫里根据复杂变动的个人数据判定你具有潜在的危险呢?他们先通过你的动态数据对你进行身份分类和定义。做个简单的假设,当你在网络上呈现出的身份里的“美国成分”低于50\%,那么NSA可能把你划分为“有潜在危险”的类别,而决定对你进一步观察或在现实中采取某种行动。 而在这个过程中,不管你是作为用户,还是公民,都感觉不到背后的监控、分类、定义,也感觉不到这些过程跟随你的社会关系而不断更新、变化。整个控制分类过程都是针对一组数据的“非政治”的、消费主义式的、不在对象身上造成任何不适体验的手段。 其后果是,我们被“置于间接和遥远的管治权力的网络里。用户个体并不能真正感受到这种算法在决定一个人的生活/生命的作用,因为算法并不与个人/个体沟通。”我们对权力控制毫不自知,因为分类的转变如此不着痕迹。但是,“围绕我们身份的潜在话语可能存在问题——让我们作为网络上的主体的定义变得越来越模糊”。我们失去了定义自己和与他人关系的权利。 更严格地说,我们正在失去对构成我们身份的那些类别的意涵的自主权。 随着新的控制类别不断被这种调节控制模式建构起来,政治的、有权利的“公民”被“非政治”的控制分类手段,变成了一个看上去非常“自由”、但被制约的“用户”。 当公民地位被降低为“用户”这种可计算的东西,我们如何理解隐私、公民权利和自我都受到影响。Bridle不无忧心地评论,由于我们从属于某个变动的类别或群体,身份的不确定性使得原本能够让我们远离各种形式的侵犯、攻击和死亡的法律保护变得不稳定或被摧毁了,那些本应包涵在公民地位里的权利和机遇也不再稳定可靠,我们变得像一个个被放逐在荒野上、不受到任何保护的人。 当政治家认真地在虚拟网络世界里协商、吵嘴、定协议,划好了国界,我们的网络国籍看上去是一副世界公民的样子,造就的却不是“政治的”公民,而是享受不到稳定公民权利的没有国家的人。 今年6月,由于俄罗斯和中国破译了斯诺登盗窃的文件里机密信息,了解到英国情报人员在各自国家如何工作,英国不得不将这些人员分别从两国移除,而且他们也不可能继续在中俄两国为英国从事有用的情报工作了。 如果说Bridle的Citizen EX项目是在网络空间勉力显示出用户“基于算法的公民身份(algorithmic citizenship)”,显像化和批判这种完美无痕的“去政治化”的统治手段,斯诺登则以“公民必要之恶”的方式(指1971年八位美国公民潜入美国滨州梅蒂亚的FBI分部,以盗窃的手段获取所有档案,将美国政府秘密监视民众、压制异议表达的行为公之于众,逼迫FBI改革了情报搜集政策,并由司法部设立了调查指引),一举让那个极端“政治化”年代的场景在我们眼前闪回。后斯诺登时代 对公民隐私保护的重视迫使美国在6月份通过了《美国自由法案》,对政府实施公民监视新增了多项需满足法院许可等限制。该法案替代之前颇具争议的《爱国者法案》。是美国对“9·11”恐怖袭击后形成的《美国爱国者法》国家安全政策的重大调整,标志着美国出现重大民意转折,国家安全与反恐不再压倒一切,公民隐私保护日益受到重视。但该法案被质疑仍然存在“无法令人接受的漏洞,可能还会允许(情报机构)大规模收集互联网使用者的资料”。 作为对斯诺登事件的回应,英国也于今年7月发布了报告,承认公民隐私应该在国家安全机构和情报部门的信息监控和搜集工作中予以更重要的考量。这份报告也同样建议实施公民监听应获得法院许可,并在监听行动实施之前将公民隐私问题纳入考量,而不是在监听行为实施的后期。 不过,这份报告遭受的批评也很多,尤其是针对“英国情报机关没有‘蓄意地’违法监听”的陈述。此外,情报机构和公民隐私保护组织仍然在监听过程中的哪个阶段应考量公民隐私存在较大分歧。 目前所有这些变化,都不足以判定我们是否能在保护公众安全和维护公民自由之间找到平衡,我们也还远远看不到公民是否能回到真正的“公民”,找回保持隐私、定义自我身份和与他人关系的自主权。 延伸阅读:Cohen, J. (2013) What Privacy Is For. Harvard Law Review, Vol. 126, 2013Dean, J. (2005) Communicative Captalism: Circulation and the Foreclosure of Politics. Cultural Politics (2005), Vol. 1, Issue 1, pp51-74The Guardian (2013) NSA Files: Decoded. http://www.theguardian.com/world/interactive/2013/nov/01/snowden-nsa-files-surveillance-revelations-decoded#section/1Cheney-Lippold, J. (2011) A New Algorithmic Identity: Soft Biopolitics and the Modulation of Control. Theory, Culture & Society (2011), Vol. 28(6): pp164-181(《中国新闻周刊》nen去发了,转载请告知。我不喜欢他们改的标题bt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