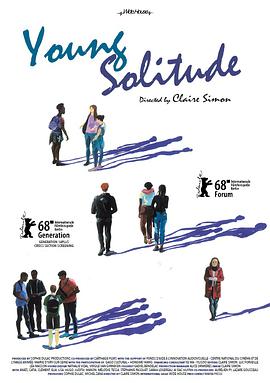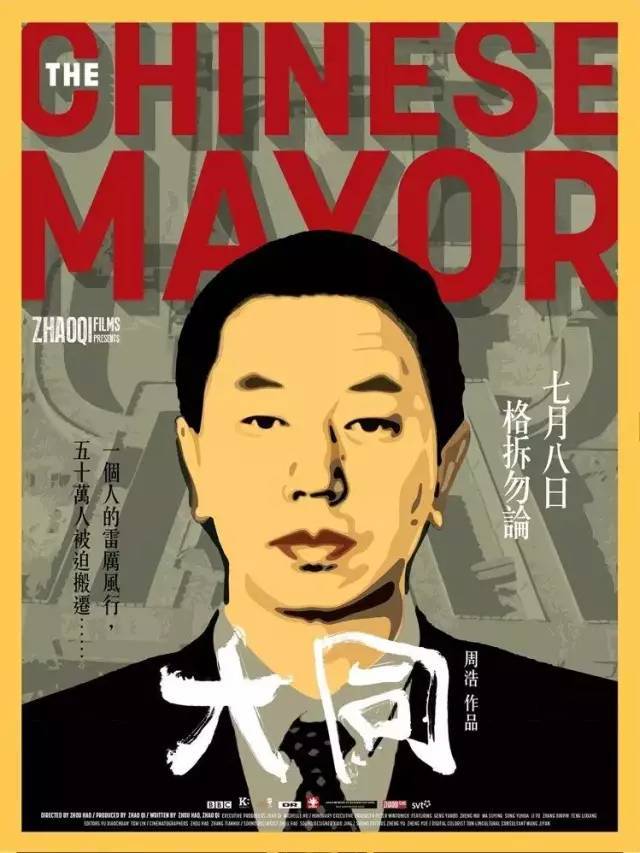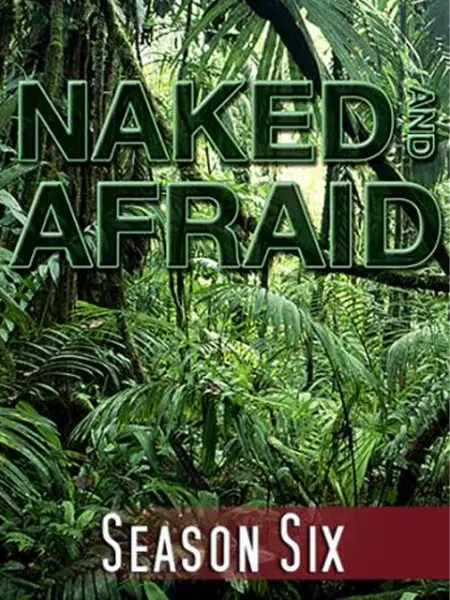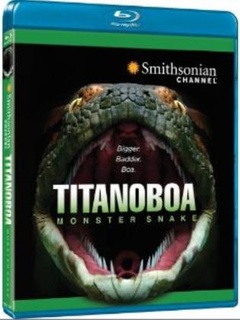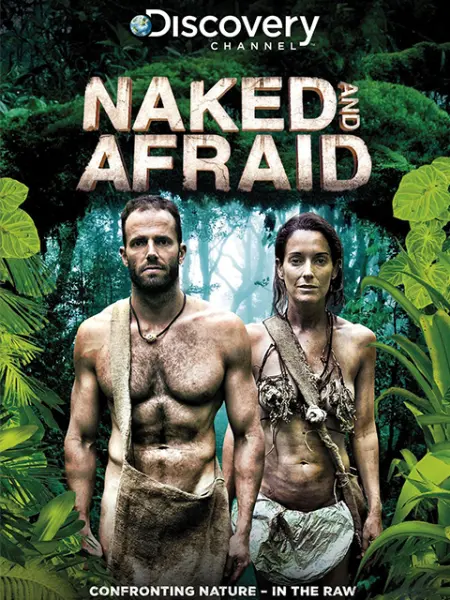@《年轻的孤寂》相关热播
@最近更新纪录片
@《年轻的孤寂》相关影评
这学期Claire Simon开了一门课叫“Ecoute”,意思是“听”,属于实践课程,以至于上课前我一直只为是讲收音的。最后一节课我们一起看了这部影片,她说‘Ecoute(听)’是她最近一年来在思考的,也是这部新片的主旨之一,更是这学期来给我们放映的所有片子的关注点。但我实在是get不到,她所强调的Ecoute对于一个纪录片电影人来讲,有何独特之处。而我是从她的课程中收益颇丰的,受益之处多是对于纪录片和故事片边界的探讨。 近些年,她的影片,多是群像式刻画。空间是比较封闭的,例如《巴黎北站》里的北站,《我们在这片森林制造梦想》里的的文森森林,包括这部,这样的封闭性公共空间适合遇见各个阶层的人。而她在《巴黎北站》跟《森林梦想》这两部中的拍摄方式也是如出一辙的,一般三个人,她、摄像、收音,有时候摄像收音一个人搞定,两个人都能出去踩踩点拍一拍。这样游击式纪录片真省钱,而且这种创作模式和数码时代也是息息相关的,之前用16mm的片子,完全则是另一套创作模式。但缺陷也是显而易见的,仿佛再牛逼的纪录片导演都面临着同样的困境:因为种种原因,他们所呈现的东西,只是他们遇到的精彩画面的五分之一,甚至十分之一。 拍摄环境的恶劣是原因之一,比如《北站》中嘈杂的收音,这部片子结尾处恶劣的夜景拍摄,等等。然而最大的麻烦还是审查。 行政审查其实影响比较小,老大哥不可能随时在场,到行政审查时,画面怎么着都已经拍出来了。至于拍摄许可,虽然是法国,但一些导演跟电影系学生交流会上,大家喜闻乐道的就是怎么偷拍,哪一场在地铁里拍摄时根本没要许可,拍完就走了,类似于此的事情,不胜枚举。 最大的审查来自于拍摄对象本身,他们面对摄影机时有人戏精上身,有人事后要求禁止使用某些片段,而这些片段在导演眼中往往十分真实美好。遗憾总伴随纪录片,于是难以自已地,纪录片的导演把手伸向了被拍摄对象——而我觉得这才是Claire SIMON在这部片中,以及一整个学期样片的主题——当纪录片导演将手伸向被拍摄对象时,导演所呈现的东西是什么? 她请来了两个人来做交流,一位是《Vers la tendresse》的导演Alice Diop,一位是《夜色兄弟》的导演Patric Chiha。这两部片子都有着纪录片的外衣,然而前者导演是社会学出身,在经过大量对城郊青年性观念的社会学调查研究后,创作了这个纪录片剧本,她甚至付钱给拍摄对象,让他们演。后者也一样有趣,学Mode出身的一位导演,听闻奥地利底层年轻同性工作者故事后,跟拍摄对象一起生活许久,拍摄对象都是真实的,然而也如同影片呈现的感觉一样,这些底层的孩子不会因为艺术而配合你,他们会一直问导演要钱。有时你则不得不说“要钱可以,把这一条拍完”。而出身Mode的导演在纪录片拍摄过程中一直只带霓虹灯,造出红色的、黄色的、紫色的光雾,也是此片最吸引我之处。 此外被引用的还有《下流故事/ Une sale histoire》,导演拍了两段一模一样的故事,一段是纪录片,一段是找演员演的;阿巴斯的《十段生命律动/Ten》,全篇主要两个机位,等等。再实验一些的,徐冰的《蜻蜓之眼》。更实验一些的,也是不胜枚举。所以,什么是纪录片,什么是故事片,在这些作品中无法被定义,也毫不重要,纠结于此没有任何意义,我们只能做出判断:这是一部十分优秀的影片。 归结到这部影片,有些网站将其定义为纪录片,有些分类为故事片,Claire SIMON自己认为这是故事片(她仍孜孜不倦地定性影片的记录或故事属性),因为她会在拍摄过程中打断被拍摄对象,然后指导演员应该把主题往哪里扭,甚至是下句话该说什么。 回到她原计划的讨论的主题:Ecoute(听)。难道听不是任何一个以谈话为主的纪录片的重要元素么?难道交流不是人的基本处境之一么?这是一个泛而又泛的主题,以至于几乎任何一部影片拿来,都能按照Ecoute(听)的路数分析两句。值得一提的是,在课上,她要求大家拍摄一些“Ecoute”为主题的实践,于是同学就把之前拍的不管是啥玩意儿都拿过来放,只要说圆乎就行。觉得这些真是毫无意义,我大概永远都get不到她这个拍摄意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