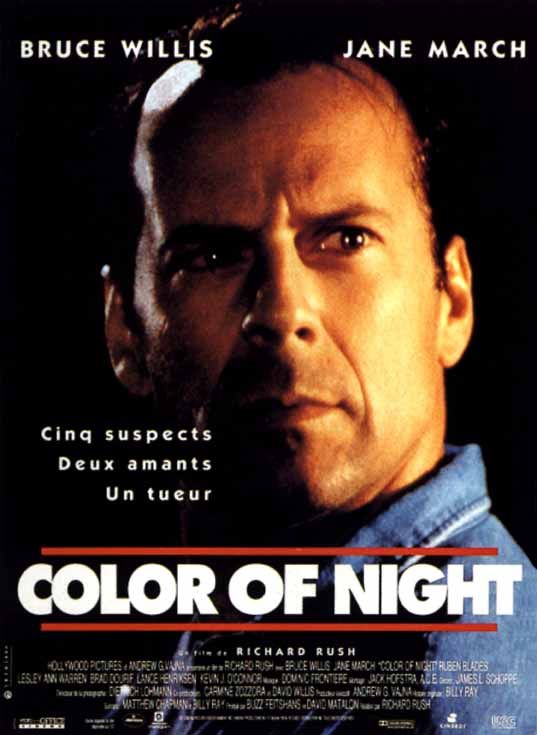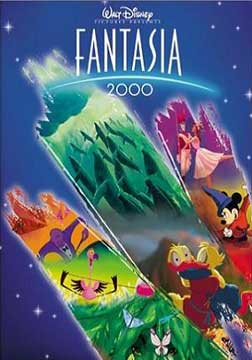@《生烟草之味》相关热播
@最近更新剧情片
@《生烟草之味》相关影评
每个人的童年里都有私人和隐秘的部分。 1997年,我四岁,全家从市中心搬往城市边缘一个中古的小区,离火车站只有不到一百米的距离,火车站前有一个带喷水池的小广场,里面的水常年都带着青苔的黑绿色,成群的黑虫在水下窥伺,雨后会有蜻蜓在空中盘旋。日光从榕树的缝隙里落下来,落在发黄的触须上。预示着雷雨将近的白色高积云成了一些空无人烟的楼房的背景,它们空洞的窗户里装着深邃的蓝天,场面荒凉而诡谲。这里是城市的边缘地带,空气里充满陌生的气味,渗透进你的全身,在血液间流走。 我在那里呆了三年,没有上幼儿园,这意味着我有大把的时间把每一寸关于这里的记忆都切实地刻进脑海里:早上的时候我和外婆一起穿过那个小广场去露天市场买菜,进去之后面对着一条向上的斜坡,斜坡上还有一栋废弃的二层楼房。回去的时候我们要穿过一条两旁满是紫荆和木棉的煤渣路,花瓣和树叶落在两旁停车场蓝色的铁皮屋顶上。在小区的大门前常会有人凑过来询问招待所或是超市的位置,我告诉他们要往哪个方向,精确到要走过几根电线杆。如果他们对我说谢谢,我会像磕了药一样挥着手臂转身跑开,跑进楼下一个生满高大杂草的花坛里。那里生着高大的芒草,蒲公英,狼戟和野蓟,还有其它一些杂草,身体里流着苦涩的汁液,长得密不透风,我和其他几个男孩把狗尾草扎成一束,拔了一捆芒草拿回家放在铁锅里熬煮,把几条白手帕染成了暗黄的枯叶色,风干后带着浓烈的苦味。为什么鲜绿的芒草能熬出枯叶色的液体——我想象着成千上万的垦荒者在土地上挥舞着锄头掘起一丛又一丛的芒草,他们穿着黑色的衣服,汇聚成一道巨大的浊流,在记忆里冲刷出一条巨大的河道,河道里又生出新的芒草,就是这般荒芜的颜色。 胡诺特·迪亚斯在《沉溺》里描述过类似的景象,因为身处一个完全陌生的异域,感官的灵敏度被调至最高,气味,光线,声响和身体的动作都被放大,试图找到新的游乐方式——“即使隔着四条街,我也能听见水池里的喧嚷,还有收音机,我想我们过去是否也这样大声。其实没什么改变,刺鼻的氯气味,警卫亭上炸开的瓶子。我用手指勾住裹塑料外壳的飓风围栏。我有种感觉他会在那里。我跳过围栏,趴在青草和蒲公英上时,感觉自己很傻。” 《生烟草之味》把这种与感官相连的记忆碎片诠释到了极致:画面出现时背景是沉默的,蹦床,一望无际的烟草地,自行车比赛,田埂上的狐狸,长满常春藤的旧房子和干净的谷仓。对白少而简短,只提供足够我们联想两人生活的一些线索:Jess的母亲留下两卷磁带后从她的生活中蒸发;Moss的爷爷奶奶在晚上会就着Connie Francis的老歌缓慢起舞。这些应该是长大后他们极少会对外人说起的。诚如我们保留自身童年的细节一样,细微的琐事足够牵连出一段与河流等长的过去,坦白就要冒着被陌生人看穿的风险。 Moss是一个害怕孤独的男孩,他在沉闷的家中找不到半点乐趣,Jess是他唯一的玩伴。只有她陪着自己在教堂里弹琴唱圣歌,把蕨类的叶子装进玻璃瓶,从河里捞起水草和青蛙卵放在显微镜下观察,在废宅的阁楼上教她跳舞。他们之间形成了一种类似姐弟的坚实关系,所以当Jess不和他说话时,他做了一个梦,梦里出现了一段《主祷文》(The Lord's Prayer)和先前的餐桌祷告相呼应,意识流地表达了Moss希望得到Jess原谅的想法。 童年的隐秘性远不止于这种与窘境的无声对抗,还有在懵懂中苏醒的对自身发源地的思考。 Jess反复听母亲在磁带里的留言,听见她说自己是个漂亮的女孩,她不知是开心还是难过,眼前反复出现自己化身为梦露,在厕所的镜子前抽着烟的画面。她的生理正在发生变化,身体里的荷尔蒙开始增加,但她的周围却只有一个尚未成熟的男孩Moss,荒草和空旷的原野。她一边忍受青春期的焦虑一边和Moss玩着乡间的探索游戏打发时间。终于,Moss生气时的一句:“你就是一个被妈妈扔掉的孩子!”戳中了她的痛处,她愤怒地拍打着自己的大腿,周围是一片安静而难过的深绿色。 她在潜意识里或许是怀疑自己和母亲之间的联系的,她用力地朝自己的身体发泄由怀疑所带来的不满和怨恨,想要找出自己是否真的曾经是她身体里的一部分。 独处时他们像两株烟草,身体里涌动着苦涩的汁液。 Jess抽了三次烟,只有和Moss在一起的那一次真正点了火,并且只吸了一口,她只是想尝一尝烟丝的味道。他们是生涩而新鲜的,所有的燃烧都不会持久,他们渴望却无法让生活散发出浓烈刺激的香味,只能彼此依赖着去修补对方的世界。 成长是一种逐渐逃离发源地的举动。城市每天都在发生变化,意味着在五年,六年之后,一些街区将不复存在,一些古旧的黑瓦红砖会变成摩天大楼的地基或花园里的装饰,过去会被一点一点瓦解,记忆没有了可供依附的实体。能被说出口的是一系列代号——来自某某城市,曾在某某街住过。大多数人没办法回忆起那些地方确切的模样,有的只是无根的,模糊的印象。对此敏感如我者会数算着一条街上有多少根电线杆,有多少盏路灯延伸到城市灰色的尽头,努力记住更多有关童年的详细数字,尽管往后的日子里那种与生俱来的孤独感仍旧不可避免。 电影的结尾,一个崭新而漫长的夏天来到了,Moss买来了烟花,Jess点燃了篝火,说了一个陈年笑话,彼此心照不宣。 "What is the biggest soda in the world?" "Minnesota." 红色的焰火从管中冲出,闪着明亮的光落进烟草地里。 散落在破碎回忆中的快乐无法言说。